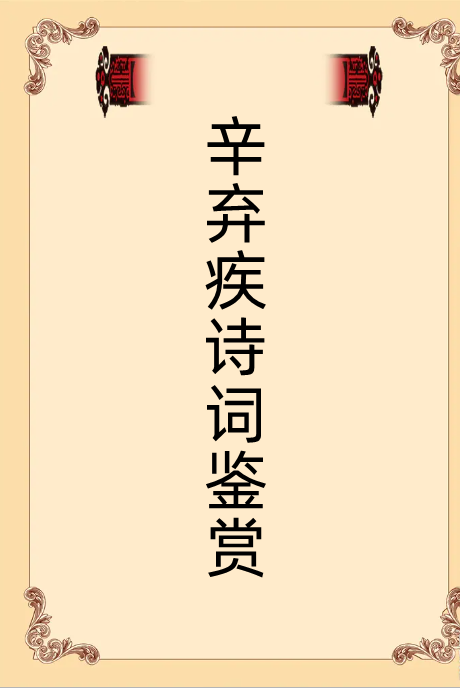立冬又见菊花黄
曹中贵
“立冬冬,藏果果,藏个窝瓜能长锅,藏个红薯饿不着,藏个枣子满嘴甜,藏个蛤蟆不唱歌。”
“立冬冬,菊花黄,满山摇曳满山香。小小儿郎快起床,光着脚丫进学堂。”
小时候,一到立冬前后,娘就哼着歌谣,一边用粗糙的大手把我从破烂的被窝里拉出来,一边帮我穿上又宽又大的补丁衣裳——那是哥姐实在穿不成了的、却又不舍得扔掉的衣裳。
现在想听娘的歌谣,只能是在梦中了。儿时的小院早已荒芜,院墙受不住风雨的侵蚀,塌了一截。屋顶上黑色瓦缝里拱出一棵拇指粗细的臭椿树,那是邻居家那棵大树撒下的种子,也许是鸟雀嫌弃籽实的味道不好随口吐下的吧?灰色的瓦松寂寞的在风中摇摆,花喜鹊落在柿树枝头,朝着红灯笼一样的甜柿“噗、噗、噗”啄几下,扭头看看没人,美滋滋的叫几声。那一棵歪脖子枣树倔强地挺立着,树梢高处的几枚红枣铃铛一样在风中叮叮作响,可是在怀念那一根长长的、一头裹着红布的打枣棍吗?
残门锈锁久不开,灰砖小径覆干苔。无名枯草侵满院,一股辛酸入喉来。如今,我也成了喊儿唤女的人了。
“为什么要藏起来呢?蛤蟆为什么不唱歌了呢?”
“为什么要光着脚丫进学堂呢?”
每当我学着母亲哼起歌谣的时候,儿子总是仰着小脸蛋儿好奇地问。那时女儿还小,听到我唱歌,就拍着白白净净的小手嘻嘻地笑。
“立冬呀,就是要把打下的粮食收藏起来,不要让小老鼠吃了。那家伙可机灵了,别看个子小,藏到粮仓里可会糟蹋粮食。”
“有的小动物冬天怕冷,要藏起来呢,所以蛤蟆就不唱歌了。”
“我小时候上学跑得远,山路上都是石头疙瘩,鞋底子磨成洞,鞋帮子裂开嘴,跑不快,害怕迟到了老师不让进教室,只能手里拎着两只鞋,光脚跑了。”
每一次我都绞尽脑汁找答案,儿子却好像从来没有听够过,只要我一哼唱这首歌,同样的问题,每次都问。
等到儿子不问了,女儿又开始一次次的问为什么,不过我不用回答了,儿子装出很有学问的样子讲:“有的小动物呀,忙了一年,累了,冬天天冷,它们要休息了,这就是动物的冬眠,所以蛤蟆就不唱歌了。”女儿便恍然大悟似的拍起手。
读了高中的儿子是勤奋的,他是从农村学校选拔到市一中的。有一年立冬正值周末,我突然心血来潮,想知道儿子的学习情况,吃罢早饭就戴上头盔,骑上摩托车,把妻子包的饺子小心的用小棉被裹了一层又一层前往市一中。沿山路上,小小的野菊花在微凉的风中无拘无束地盛开,风里透着缕缕清香,那是无数小生灵在欣喜地炫耀生命的璀璨。我赶到时已近中午,阳光暖融融地照进教室,几个没有回家的学生正专心致志地学习。
我喊了孩子,把饺子交给他。他边吃边说:“我突然想起小时候你唱的‘光着脚丫进学堂’了,其实正是因为进了学堂,才知道光着脚更要奋力拼搏的。”
停了一下,孩子又说:“我小时候你给我讲的立冬不完整,古时候民间习惯以立冬为冬季开始,与立春、立夏、立秋合称四立。”
“都过去十多年了,你还记着这话?好呀,比我知道的多了。但那是你奶奶唱给我的,我又唱给你听了。”
这算不算家庭文化的熏陶?或者说是一种朴素的精神传承呢?
今年秋天,孩子高校毕业。再有几天就该立冬了,我俩相约在家乡的山坡上随意走着。“园林尽扫西风去,惟有黄花不负秋。”放眼望去,田间地头,岭上岭下,一丛丛、一簇簇的野菊花把空旷的山野涂抹成一片金黄。碧蓝的天空,南飞的大雁跨山越河,抵达它们向往的地方。
“爸,咱俩一起唱我奶奶教你、你又教给我的歌谣吧?都快忘了呢!”
“好呀。”我扯开喉咙唱:“立冬冬,藏果果,藏个窝瓜能长锅......”
唱着唱着,我想起了故去的爹娘,想起他们把放干透了自己也舍不得吃的白面馍压碎,用热水泡泡,撒一些白糖,搅动几下喂我嘴里的场景。于是,风里除了花的香,多了一丝哀伤。